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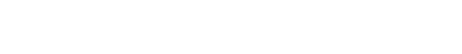




大阪大學教授阪口志文榮獲202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京都大學教授北川進榮獲2025年諾貝爾化學獎。
同為東亞文化圈,日本諾貝爾獎獲獎頻率井噴式爆發,在2000年後迎來黃金時代,這對中國人來說,也是值得共勉的好事。
長期以來,亞洲人得不到科學領域諾貝爾獎,被視為一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尊龍凱時人生就是博,中國和日本是被歸在一起的,是被歐美人當作“科學”(贏學)研究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Kanazawa與Miller的爭論。
2006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進化心理學家Satoshi Kanazawa和新墨西哥大學進化心理學家Geoffrey F. Miller,在《Evolutionary Psychology》期刊上展開一場備受關注的辯論,焦點是進化心理學的未來發展方向,是否應將重心轉向亞洲尾隨單機遊戲。該辯論源于Miller對西方學術衰落的擔憂,並迅速演變為對東亞創造力、文化與遺傳的激烈爭論。
Miller預測,西方進化心理學面臨“老齡化”危機,資金短缺、學術自由受限尾隨單機遊戲、政治正確扼殺創新。相反,亞洲國家如中國、印度、日本具備人口紅利、科研投入激增,特別是中國的GDP增長尾隨單機遊戲,將成為“救星”。他呼籲西方學者“轉向東方”,利用亞洲的“嚴謹性和勤奮”推動領域發展。
Kanazawa強烈反對,稱Miller的願景“天真且危險”。他還斷言,亞洲擅長工程這樣的應用科學,但基礎科學需“框外思考”,東亞難以產生“原創想法”。他嘲諷,若Miller生于中國,其工作將“數學化但不可讀”。
Kanazawa明確表示,出于文化、社會和制度上的原因,亞洲人無法對基礎科學做出原創性貢獻。Kanazawa提供了一份關于諾貝爾獎得主國籍的統計數據,以此證明亞洲國家在原創性科學成就方面的代表性不足。當時,諾貝爾獎得主數量最多的前五個國家(美國尊龍凱時人生就是博、德國、英國、法國、瑞士)均為歐美國家,截至2005年,曾產生諾貝爾獎得主的亞洲國家有九個,最多的日本也不過只有12位,Kanazawa 強調,如果將諾貝爾獎得主數量按人口標準化來衡量(相對代表性),所有亞洲國家都處于代表性不足的狀態(數值小于 1.000)。例如,日本的相對代表性為0.7789,印度為0.0526,中國為0.0377。
相比之下,前四個歐美國家(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的諾貝爾獎得主數量按人口計算被高估了5到10倍,而瑞士更是被高估了28倍。Kanazawa指出,日本作為20世紀大部分時間裡的主要地緣政治和經濟大國,僅產生了12位諾貝爾獎得主,與奧地利數量相同,但奧地利的人口僅為日本的十六分之一。
Kanazawa認為,諾貝爾獎的統計數據清晰地表明,科學本質上是精英主義的,國家通過擁有好的想法而不是龐大的人口來主導科學。他總結道,亞洲在過去一個世紀裡似乎缺乏好的、原創性的科學想法尊龍凱時人生就是博。
他指出,東亞專家早就將此問題稱為“創造力問題”。雖然東亞人在平均智商(IQ)上略高于歐洲人,但他們未能創造性地利用其智力。他們擅長通過死記硬背吸收現有知識,因此在數學和科學的標準化測試中得分高,或改編現有技術,因此在工程方面取得成就,但未能對基礎科學做出原創貢獻。Kanazawa認為,正是文化、社會和制度因素的某種組合抑制了亞洲的基礎科學發展。
Miller在回應Kanazawa的評論時,雖然承認Kanazawa的諾貝爾獎數據是準確的,即亞洲科學家在科學創造力的這一極端門檻上確實處于代表性不足的狀態,但他認為根據這些數據推斷未來是非常困難的。
在1901年至1925年間,德國裔研究人員在物理學、化學和醫學諾貝爾獎中佔據了主導地位。相比之下,美國本土出生的研究人員在同一時期僅獲得了極少的科學諾貝爾獎(物理學1個,化學1個,醫學0個)。
Miller認為,如果在1925年僅憑諾貝爾獎數量判斷,當時歐洲人可能會認為美國反智主義、實用主義和政治腐敗等文化因素會繼續抑制美國的科學創造力。然而,美國科學最終仍然取得了統治地位。
Miller還駁斥了亞洲存在普遍“創造力問題”的說法。他引用了 Charles Murray (2003) 的研究,該研究記錄了亞洲在藝術、文學和哲學領域的顯著創造性成就。他特別提到,西方歷史學家逐漸意識到,歷史上歐洲所做的幾乎所有事情,中國都做得更早、規模更大、技術更好,例如中國航海家鄭和的船隊規模遠超哥倫布。
Miller認為,創造力依賴于一般智力(IQ)與經驗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一種人格特質)的相互作用。他同意東亞人具有較高的平均智商。他引用了 McCrae (2001) 對 26 種文化進行的“大五”人格特質研究,結果顯示亞洲文化的平均經驗開放性得分與美國(設為 100.0)相似,部分亞洲國家甚至略高于美國。Miller認為,亞洲擁有與美國相似的“開放性”水平,加上更高的智力潛能和龐大的人口基數,其科學未來大有可為。
Miller承認,當前的亞洲教學風格通常強調死記硬背和分析推理,而不是自我表達的創造力。同時,Kanazawa認為亞洲文化具有從眾性,不利于挑戰現有範式。Miller反駁道,有研究表明,亞洲學生的社會化從眾性是容易克服的,只需明確指示他們“要有創造力”,或強調創造力對集體的好處,這在研究生科學教育中是常見的做法。
Miller還反駁Kanazawa的“種族主義”傾向,認為東亞諾貝爾獎少系歷史滯後,包括殖民/戰爭等原因,而非內在缺陷。日本2000年後物理/化學獎獲獎增多,證明了其潛力尾隨單機遊戲。他贊揚東亞“漸進創新”(incremental creativity),建議西方學習亞洲的“集體智慧”,而非一味貶低。
這場辯論未止于期刊,而是迅速擴展到博客、媒體和學術圈。Kanazawa的極端表述,如亞洲“無法產生諾貝爾級想法”被指“偽科學”和“東方主義”。
Scott Barry Kaufman在Psychology Today(2011)發文稱Kanazawa觀點不代表領域主流。2011年,68位進化心理學家聯署公開信,譴責Kanazawa的“壞科學”不具代表性,強調進化心理學注重證據而非刻板印象。
Kanazawa在博客和後續論文(如2009 “IQ and the Values of Nations”)整合辯論,嘗試用“薩凡納-智商假說”(Savanna-IQ Hypothesis)解釋現代環境不匹配進化適應,導致東亞高IQ但低創造。他將辯論擴展到智商研究,稱亞洲“過度成就”僅限于學生階段。
而延續Kanazawa觀點,為什麼東北亞人獲得如此少的諾貝爾獎,這個主題在以此為題目的論文Kura et al. (2015)中被繼續討論,幾位作者用基因,如DRD4好奇心等位基因來解釋東亞的低原創。
這篇論文的核心論點是,東北亞人在科學成就上表現不佳,不是因為智商低,而是因為在“好奇心”和“獨立思考能力”等關鍵心理特質上低于歐洲人尊龍凱時人生就是博。
論文稱,截至2014年,歐洲人平均每百萬人獲得了0.6個諾貝爾科學獎和菲爾茲獎,而東北亞人尊龍凱時人生就是博,指中國、韓國、日本平均每百萬人僅獲得 0.03 個尊龍凱時人生就是博,大約是歐洲人的二十分之一。
另一方面,東北亞人的平均IQ被報道為105,高于歐洲人。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等數據顯示,他們在學校學習成績上也持續優于歐洲國家。此外,在美國,亞裔學生在精英大學和各類學生獎項中的比例嚴重超高,這表明他們相對于其IQ而言是“超常表現者”(overachievers)。
既然智商很高,但原創科學成就卻很少,作者認為原因在于人格差異,這種差異有基因分布基礎。為了衡量這種差異,作者構建了一個名為“q 指數”的指標,用于衡量好奇心和獨立思維能力。
該研究認為,智商(IQ)得分和指數都對人均諾貝爾獎數量有顯著貢獻。在分析中,當僅用IQ預測時,模型只能解釋5%的差異;但加入q指數後,模型能解釋19%的差異。歐洲國家在q指數上的平均分比東亞國家高出約1.4個標準差尾隨單機遊戲。
q指數包括了三種對于“卓越科學成就”至關重要的心理特質,這些特質由特定基因頻率來代表。DRD4基因的7-重復等位基因與新奇事物尋求行為(novelty-seeking)和衝動性相關。歐洲人、非洲人中約有20-30%攜帶7-重復等位基因,但中國、韓國的頻率是0%,日本是1%。作者聲稱,該等位基因可能在過去30000年中被選擇性地從東亞人群中移除,可能是因為它幹擾了社會和諧。
5HTTLPR基因的長等位基因能更有效地運輸血清素,從而穩定情緒並減少攜帶者的焦慮。東北亞人攜帶長等位基因的頻率約為20%,而歐洲人約為60%。但作者沒有直接說明這種特質如何影響科學成就。
OPRM1 G等位基因與對社會排斥的恐懼有關。攜帶G等位基因的個體在被排斥時會表現出更強的不愉快感。作者認為,偉大的科學家必須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能夠堅持新穎的想法,這與個人主義緊密相關。當目標由國家或組織設定時,追求個人價值會困難得多。歐洲社會具有高度個人主義,而亞洲社會是集體主義的。作者發現,亞洲人群中G等位基因的頻率遠高于歐洲人群。這種文化上的差異(歐洲和東北亞之間差了1.98 個標準差)限制了東北亞地區原創科學突破的產生。
這篇論文也討論了其他可能解釋東北亞諾貝爾獎稀少現象的因素,並對其進行了反駁。有人認為二戰前日本的生活水平較低。但作者反駁說,如果IQ較高尾隨單機遊戲,為何生活水平會低?而且自1970年左右日本生活水平提高並超過西歐後,其科學成就仍然較低。有人認為東北亞人IQ分數更集中于平均值(基因同質性高),導致極高IQ的人才更少。作者認為,由于科學成就需要高智商和高指數,這不太可能是唯一的解釋。
還有人推測,在20世紀許多歐洲諾貝爾獎得主出生時,歐洲的平均IQ可能高于東北亞。但作者指出,即使只看1980年後,日本和韓國的成就(日本17位,韓國0位)仍不如英國(22位)和法國(19位),即使考慮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平均IQ。
把不同國家、族群的諾貝爾獎數量問題作為研究題目,探究原因,本身當然也可以是一種“科學”。進化心理學強調行為的遺傳基礎和跨文化、跨族群的差異,這一論題既符合其學術使命,又深得贏學真傳。
隨著近年來日本的諾貝爾科學獎數量越來越多,“50年拿30個諾貝爾獎”的願景可能提前實現,亞洲的逆襲已經發生,我們今天再回顧上述的那些“西方學術”,就更能生出“終究不攻自破”的感慨。
日本于明治維新(1868年)開啟現代化,成為亞洲首個工業化國家,到1930年代,已建立完整科學體系,甚至在二戰前就產出諾貝爾級成果,如湯川秀樹的粒子物理成就。饒是如此,日本的科學諾貝爾“黃金時代”主要還是集中在2000年後,遲到了太久。日本有100多年的“遺產”緩衝,允許科學家專注長期基礎研究,而非趕超工業化。
按Nature Index,中國的科研產出已經全球第一,按R&D投入,韓國佔GDP 4.8%也世界領先,但卻都鮮有諾貝爾科學獎。韓國工業化從1960年代起步,中國科學體系在改革開放後才重啟,歷史積累,還沒到時候。
那臨界點在何時,恐怕就在中國走過趕超工業化的階段,走到前沿,走到無人區的時候。諾獎評委,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鄒曉冬教授最近在採訪中表示,按照中國現在的發展趨勢,諾貝爾獎已經越來越近。
她還說,中國科學家需要有發現一個空白且重要的領域的能力,能夠把精力用到這個領域上,做出從0到1的工作。而不是被影響因子和文章引導,在別人已經從0到1開拓出來的領域去做那些熱門的研究。此外,中國科學家應該“打出國門”,跟國外的人多交流,要“卷”也要到國際學術圈來“卷”。
前文介紹的Miller,在2006年就能看到西方學術衰落和東方創造力的崛起,轉眼又要20年過去,諸君還在猶疑什麼,“卷”起來吧。尊龍凱時人生就是博!!尊龍凱時app下載上海景點,天文學尊龍凱時平台登錄尊龍凱時app下載,尊龍凱時 - 人生就是搏!平台。拉斯克醫學獎。